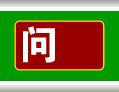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 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道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过,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
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体会尤甚。所以我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降生在什么地方相当重要。20年前插队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我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他们没有机会上学、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便只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变,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我希望我的来世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这样是不是就好呢? 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 ·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虽好,不过在哪儿呢?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 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的童年,当是莫大的缺憾。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做你的朋友,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当你父母不在家时,把好朋友都叫来,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载歌载舞地庆祝。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拿点钱,瞒过父母,然后出发,义无反顾。
把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没关系,你母亲不会怪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跪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撒尿和泥,然后不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时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做些别的事,让你父亲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熟人都对你刮目相看,各种奖啊奖啊奖啊并不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雅的歌剧,粗犷豪放的民谣,你都听得心醉神迷。你喜欢美术,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体育也是你的擅长,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那是舞蹈,是人间最自然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辉煌的艺术形式。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呵又闹着找你,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但你一向只是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东西。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于是你不跑了,光是看她。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操场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们到底认识了,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你们终成眷属。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顺利、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 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颠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 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阴塞了渴望,限制了想象,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遵从了一种生理程序,心路却已荒芜,继而是麻木----会不会?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 很明白,那是死亡。
如果你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已入绝境。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路,当然你也跑不了。其他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它了。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现实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
过程! 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